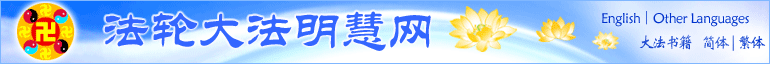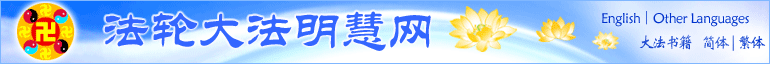【明慧网2001年12月24日】1、亲戚
从劳教所一出来,我知道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我远在家乡的妹妹从去年底在天安门炼功被抓又走脱后,一直流落在外。而警察为了找她,连最偏僻的乡下远亲都没有放过,一一骚扰到了。
我离开家乡十几年了,有很多亲戚已多年没来往过了,但这次我特意旅行几千里地,一一拜访了他们。每到一家,我都先说:这一年来,因我和妹妹的问题让你们担惊受怕了,我这是特意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亲戚们一听之下,都很感动。由于有充份的时间,我很自然地就能找到适合不同对象的角度向他们讲真相或洪法。劳教所的残酷让亲戚们心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由于自己的善心和对我的亲情而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同情大法、反对迫害的一边。连十分反对我继续“冒险”的不修炼的另一个妹妹,也出于对我的尊重和亲情跑出几百里地去给我借了台手提电脑,好让我给明慧写文章,还教我怎么安全上网。
2、同学朋友
从家乡回来,我又给同学朋友打电话。许多人并不知道我被劳教的事。于是我在电话里先说:“好久不联系了,没骂我吧?”
“哟,是你呀!这么长时间你逍遥到哪儿去了?”
“嗨,甭提了,劳教所!”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真的,不骗你!我炼法轮功你知道吧?就因为炼法轮功劳教了一年!这不刚出来就赶紧向您汇报汇报。怎么样,请我吃饭、给我压压惊吧?详情我们见面再谈。你能再把谁谁谁也叫上吗?”
就这样,我把能约到的同学朋友或约到家里,或约到饭馆。见面时我自然是谈话的主角。所有同学朋友都知道我在学校曾是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也都知道我毕业后有几年病得死去活来,什么同学聚会都参加不了。于是我讲自己修炼后身心两方面的受益、讲这场镇压的荒唐、讲电视里的宣传全是造谣、讲劳教所的黑暗……因为是多年的同学朋友了,当然谁都相信我。
3、其他人
去年初第二次从拘留所出来后,我结识了一位教授。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饭馆,他和他夫人专门设宴为我“接风”。
我那天谈了四个多小时,谈话中我经常引用老师的话。每当我背诵老师的经文时,他和夫人都挺直腰板,背部离开椅子靠背,凝神倾听,脸部放光;经文一背完,他们就重新靠了回去,听经文时脸上特有的那种光彩也消失了。这个小动作和脸上神情的变化重复了许多次,他们自己却完全没有察觉。
后来我被绑架进劳教所后,教授曾去看过我多次,甚至曾想利用自己的“关系”将我救出。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到教授所在的学校去帮忙做一些外事工作。
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特别棘手。学校与一个英国人合作办了个英语教学点,因为沟通的问题,双方关系搞得很僵,英国人拖欠了许多管理费没交,而学校则卡着发票不给他们用。
我到了那个教学点,英国人一肚子火,也没什么好脸色给我,劈头盖脸先来一通抱怨。我当然得站在学校的立场上据理说话。说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他突然问我,我知道你们学校的薪金很低的,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外企或是到我这里,起码能拿七八倍的钱,为什么要在那里干呢?
我沉吟了几秒钟,诚恳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给你。我是炼法轮功的,刚从劳教所出来;在劳教所时教授曾很关心我。我困难时他帮助了我,现在我再帮他。我不图钱。
这个英国人到中国很多年了,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受过很多次骗,为了保护自己,学得几乎要跟那些不讲信义的中国人一样了。他也知道现在在中国公开称自己炼法轮功意味着什么,而且我们几秒钟之前还在“吵架”。我这样的中国人他从没见过。
他也沉默了好几秒钟。再开口说话时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后来我们再见面时他虽然绝口不提法轮功的事,但我看得出来,我的“秘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在坚持学校利益的同时,也充份地体谅他的因难,检点学校方面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先从自己做起。其实无非是一个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和责任心的问题。后来他亲自开着车把欠学校的钱全数送来了,并对校长说我有一个最优秀的谈判者。
这一日学校来了一个访问团,由北美两所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学校请了一个讲师给访问团讲中国文化和历史,我坐在一边旁听。讲完后一个学生问了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讲师的回答完全是照本宣科,脱离现实。
听完课学校宴请访问团,我继续作陪。虽然从学校毕业后有十年都不用外语了,讲起话来很费劲,我还是硬着头皮对刚才提问的学生说:“我不太同意刚才那位讲师对你的问题的回答。在中国,理论上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起的作用很小,基本上是党指挥一切。以法轮功的问题为例,先是中央极少数人决定了要镇压,然后将整个国家机器都调动起来。等发现镇压缺乏依据了,再逼着人大去这个那个。就说我自己吧……”然后我就将自己因修炼刚被劳教一年的事情讲出。当讲到劳教所为逼我“转化”将我电得晕了过去时,饭桌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几个女学生眼里含满了泪。吃完饭后,好几个女学生特意走过来感谢我与她们分享我的故事,一个男学生告诉我他的祖上就是因为在欧洲受宗教迫害才逃到美国的,而一位带队的教师则对我说,她很想进一步了解我所信仰的。我给了她大法的网址。
后来学校与来访的美国大学签定了互换教师的意向。带队的美国教授说有可能的话,将争取在明年安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
我正愁没有机会向她讲真相,她这么一说,我趁机要求单独与她见面。我开门见山地谈了自己的遭遇,直截了当地请求她的帮助,并告诉她因为我不但还在信法轮功,而且还想揭露劳教所的黑暗,所以处境很危险。
其实我早已悟到只要正念强,一定不会再被抓,也不是很在意她是否会帮忙。但就象师父说的那样,“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李洪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的演讲》)。我个人的体悟是有时候面对善良的人,你如果能真心实意、大大方方地请求帮助的话,比单讲真相效果更好,因为他们的心会被牵动,他们会把自己也牵扯到与大法有关的事情中来,并觉得他们跟我们是“自己人”。这样对他们更好。
她当即答应担保我去美国。回美国后果然在最快的时间内办好了邀请我去她们学校做访问学者的手续,发来了邀请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教学计划和人员安排早就做好了,一般不会临时更改。我知道她费了很大的劲。虽然后来我没有去,但我相信她今日的行为为她的未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那以后,她还格外关心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华盛顿邮报》上登了篇报导法轮功的文章,我都还不知道,她倒给我发过来了,并告诉我她还将这篇文章打印了,带到了学校给她的学生看。
有一次学校有个英语老师问我哪里能买到英文版的佛家著作,因为有一个在学校教英语的美国大学生问她而她不知道。我直接给她拷了一张盘,里面有《转法轮》的英文版,盘的标签上写上了大法的网址,让她给那个美国学生,并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佛家著作。
这个老师早已知道我所有的事,所以也没有大惊小怪的就给他了。
几天后那个美国学生找到我谈了很久。听了我的经历后,他告诉我他有个朋友是加州大学新闻系的,问我愿不愿意将我的故事讲给他的那个朋友。
还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一位丹麦人,他是为一家学校做顾问的,来替这家学校谈与我们合作办学的事宜。
闲聊中我谈到我以前也做过投资顾问,他随口问那你现在怎么跑到学校搞起外事了呢?这行业跨度也太大了吧?
我说,哎,这说来就话长了,然后自然地就讲了自己因炼法轮功被劳教的事。他听了一路,最后摇头叹道:靠强制统治人心是不行的,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曾经有过“劳动光荣”(可能不准确,我的英语听力还不十分可靠,他又有丹麦口音)之类的话。
还有一次我去陪十几个志愿来中国教英语的外国大学生吃饭。好长时间也找不到机会切入,干脆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所有人都停下吃饭望着我。然后我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这些大学生全是基督徒,我讲完后有人问了我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相信基督所说的只有一个上帝吗?你们法轮功怎么看我们基督徒?
要表达清楚这个问题,我的英语还远远不够,但我一字一句捡最简单的词汇说,炼法轮功之前,我是不信神的,不信上帝的,我看到学校里在圣诞前夜举着蜡烛在瑟瑟寒风中祈祷的外国留学生时,曾觉得他们很可笑。我炼了法轮功之后,才第一次读《圣经》。这时候我不但相信,而且觉得自己完全理解《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我相信在耶稣的天国里,确实只有一个上帝;但我也相信浩瀚的宇宙中不止一个天国。每个人修炼的目的应是返还他先天生命来源的地方去。我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何方,但我相信只要修炼法轮大法我就一定能返回去。
听完这番话后,问话的人连连点头,似乎还算满意。在此我也想向同修请教对这样的问题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回答方式?
这一类的讲真相的小故事还有很多,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果不是明慧的编辑倡议大家多写讲真相的小故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它们。我的体会是只要用心,面对所有人,都总能找到机会和切入的合适角度,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对正法这件事情用的心大小”(《李洪志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只要用心用意,又有平时学法修炼的基础,是应该能“随机而行”,针对不同对象和情况最恰到好处地讲真相的。法中自有智慧和圆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