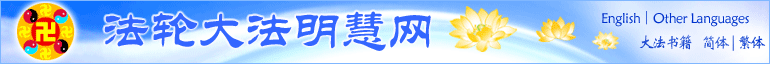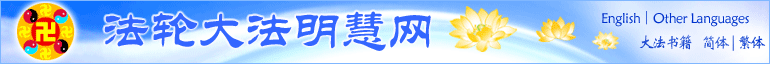【明慧网2000年7月16日】 6月19日与赵昕一起在公园炼功被抓的一些功友被放出,下面是他们的一些回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赵昕对大法的坚定,以及公安部门对无辜善良的大法学员的残暴。 (一)任何打击法轮功的事我都不会配合
--记赵昕用生命维护大法点滴
2000年6月19日晚,我与赵昕是在紫竹院牡丹亭炼功一同被抓。从炼功点到派出所,最后到拘留所,赵昕始终拒绝配合警察的工作。她是被4个警察从牡丹亭抬到警车上,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又被拖着进去。警察想尽办法让我们最后剩下的5个人说出姓名,并列举各种理由说我们此种做法不对。赵昕当时坚决地说:“任何打击法轮功的事我都不会配合。”6月20日傍晚,紫竹院派出所要将我们转移到别处,她说:“除非放我们出去,否则哪也不去”。我与赵昕和另一功友三个女孩紧紧抱在一起,四五个警察将我们强行拉开,带上手铐,弄上警车,我和赵昕不在同一辆车上。我到看守所登记处时,赵昕与另一位功友已先被带了进去。她盘腿坐在地上,面带微笑,神情坚定。后来她是被警察用三轮车运到筒号里的,又被拖进医务室检查。
我最后一次见到赵昕是6月22日上午10点30左右,我被第二次提审回来,她坐在号房的走廊里,身上挺脏。她看起来比较疲倦,但身体状态还比较好。
(二)我的被抓经历
我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6月19日晚,我和一些功友在紫竹院公园牡丹亭炼功。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在炼静功,突然从周围冒出来一群警察,叫嚷着:“都起来,别炼了,跟我们上车。”然后把炼功音乐的录音机关了,有的人起来跟着警察走了。我没理这些,继续打坐炼功,有警察过来,踢了踢我,叫我别炼了,我没动;把我的脚扳开,我又盘上;当时,我心中想起了《大曝光》中师父引用别的弟子的话“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那警察见没办法,就到一旁等着去了。其他几个功友也没理会那些警察,他们拉扯了一阵子,看看没有用,就在一旁呆着看我们炼。过了好一阵子,可能觉得他们人数够了,够几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人了,就强制性的把我结印的手分开,两个警察一人架着我的一个胳膊,沿着满是台阶的石头铺的小路,把我拖到警车上去了,当时有几个游客看到了这一情景,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感受。另外几个功友可能也是这么弄上车的。
警察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屋子里,屋子中央有一个乒乓球台,里面已经聚集了先被抓来的大约有二十几个功友,年龄不等。我们沿着墙坐着,开始背《论语》、《洪吟》,开始时警察还来干涉,后来见我们很坚定,也就不管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一个个的提审问话,无非是姓名、地址等等。一部分功友如实说了,就被送到别处去了;我们六个人没报姓名、地址的,就继续留在那屋子里(后来有一个功友跟便衣聊天时,不经意透露,后来也不知送哪去了)。警察提审我时,一开始见我什么也不说,就用手打我的脸,揪我的头发,后来看着实在不行,也就不再问了。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功友悟到,我们没有违法,不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能帮着他们干坏事。有两个女功友,其中有一个叫赵昕,被警察提审时,因为不去,警察硬是把她们拖出去审问了。
提审回来后,我看一个功友正在打坐炼功,于是我也盘腿炼起功来。不一会儿,进来一个警察,大声说:“这儿不能炼功。”我没理会,他说了几次后,见我还在炼,就扳开我的腿,“啪、啪”重重地给我几个耳光,并把我掀倒在地,我又坐起来盘上,他气极败坏地又打了我一顿。后来,我悟到自己有争斗心在,就没再继续炼下去。不过,我们以后炼功就没有人来干扰了。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大屋子里呆了差不多24小时。
21日晚6、7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功友说,我们应该要求警察放人,我们把屋子打扫了一遍,正准备去跟警察说,警察来了,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送到别处,当时赵昕跟我们说:“我们不能这样让他们带走,我们没有违法。”我们几个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警察来叫的时候,我们没动,后来,警察硬是把我们拖上车。在这期间,赵昕她们三个女功友紧紧抱在一起,警察把她们三个的手都铐起来,拖上车。赵昕与我在一个警车上,有三个警察在里面看着,她仍带着手铐。开始我不知道她被铐得很紧,因为她一直很坚强,手铐动都没动一下,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后来快到的时候,发现她在动那个手铐,才知道被铐得很紧,手腕上就露出深深的手铐印。我叫那警察给她松一下,他说:“呆会儿到了再松开。”就这样一直到海淀看守所才松开。在看守所搜身的地方,我看到赵昕还是盘着腿的,从那些警察嘴里才知道,她可能一直都是被拖着走的。
当天晚上,没有办任何手续,我就被关到了海淀看守所,至此就开始了我的监牢生活。进去的当晚,牢头就要我站在后边,美其名曰“值班”。其实这也是一种折磨人的方式,不让睡觉。当天晚上,里边的一个犯人跟我说,以前这儿也关过几个炼法轮功的,向他介绍过,他也觉得挺好,想要炼,但在这里一直没让炼过功。当时,我心里想,我要在这里开辟一个炼功的环境。但是很遗憾的是,虽然经过几次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由于两天没怎么睡觉,也没有吃过东西,进监号第二天,我感到又累又困,浑身无力,好像都快支撑不住了,我心里想着,如果再不让睡觉,我怎么过得了这关啊。我想着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突然,心里冒出一念,这不是要去我睡觉的执著的吗?想到这,我精神为之一振,以前那种又累又困的感觉顿时消失了,我重新变得精神起来。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真的是这样。
在被关押的十多天里,我就睡了一个晚上的觉,其余的时间,由于我不说姓名、地址和坚持要炼功,牢头就专门派两个人24小时看着我,晚上站着、白天坐板,不让我睡觉,甚至我一闭眼睛,他们就用拳头打我的脸和头,揪我的头发,拿凉水从头上浇下。有一次,我被他们用凉水浇完之后,浑身直打哆嗦,不住地发抖,象是掉在冰窟里一样,一阵阵发冷,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恢复过来。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基本上能做到微笑着面对这一切,丝毫没有对他们产生怨恨的感觉。由于要炼功,所以挨打有时候就成了家常便饭,犯人们动不动就可以给我来一拳。
师父说:“世人不仁,神也不神,人间无道,正念何存。”在监号里,牢头不让我跟其他人说法轮功的事,因为牢头说了,其他犯人想了解的也不敢跟我聊。这样,我只能有时候跟他们偷偷地说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怕听有关法轮大法的事,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正念,于是我就开始大声的背《洪吟》,见我这样,那两个看着我的人就打我嘴,几个人按住我,用毛巾硬往我嘴里塞,说:“看你还念,看你还念。”直到我不能出声。有一次,一块毛巾塞进去,他们捏着我的鼻子,差点让我不能呼吸。还有就是用毛巾绑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把我的下嘴唇都勒肿了,勒出了血。一次一个警察看到那些犯人在折磨我,就问头号怎么回事,犯人们说我是炼法轮功,他就不管了。我告诉管教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他说我是自找的。我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啊,我们这些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因为要炼功,就被无情地或关押、或劳教、或判刑,在监狱里可以随意地被犯人打骂,任意对待,成为不是犯人的“特殊犯人”。我知道,我所受的这些苦还是较轻的,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一块抓进去的另一位功友赵昕,在看守所里被打成4、5、6节颈椎粉碎性骨折,现在仍在海淀医院里,医生说即使治好了也要高位截瘫,可她进去之前还是一个有说有笑的非常健康的人啊!
我写出来这些东西,不是想要说明我受了什么苦。其实,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并没有感觉受什么罪,只是为不能让监号里的人更多更好的了解法轮功而感到遗憾;我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想让更多善良的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现在政府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那些善良的民众的;也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关心赵昕的事,因为当赵昕家属执控告状去海淀区检察院时,该检察院却不受理,说:“控告状上的被告人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是个单位,你们应该控告具体的人,否则无法受理。”我不相信这是不受理的理由,因为我虽然不太懂法律,但也知道被告人可以是单位的。希望政府能够惩恶扬善,而不是惩善扬恶,颠倒是非!